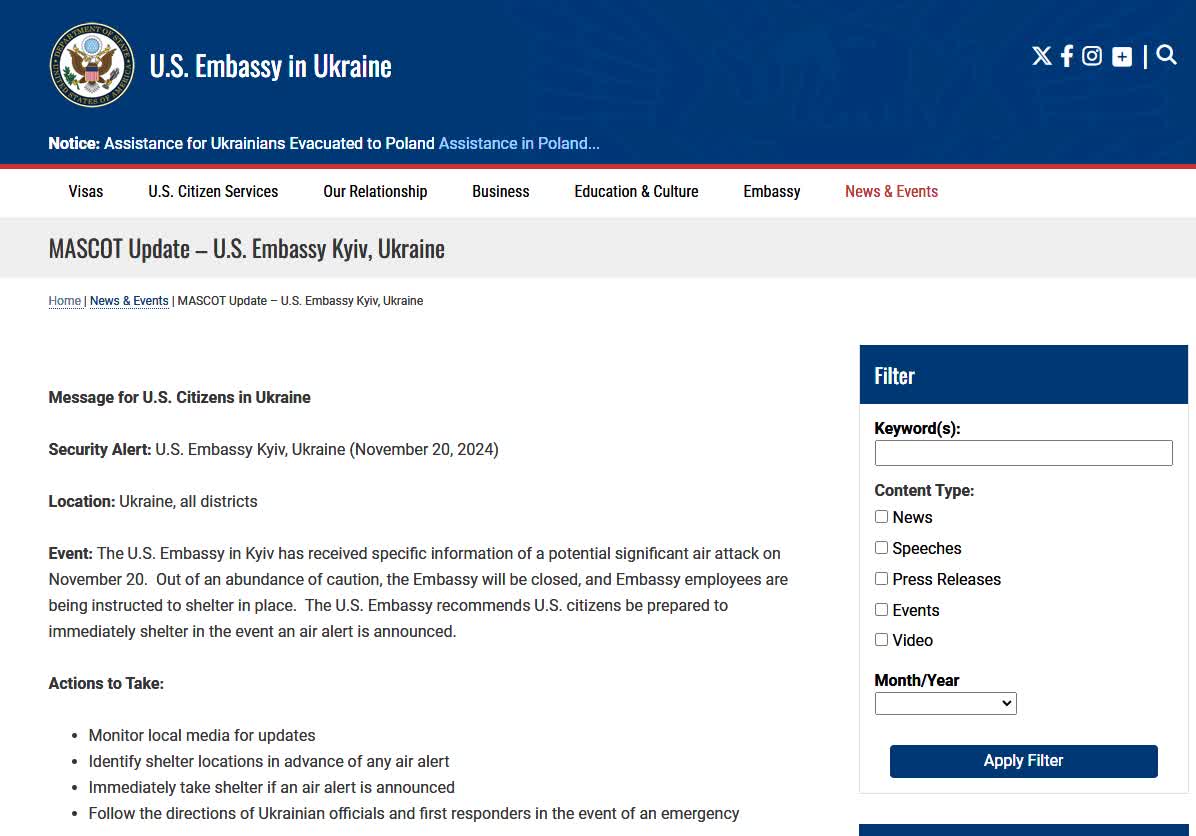文:邱怡青
對她來說,專訪著故走再家從未真正的吳俞溫馴興起落成。
她一直帶著行走,萱帶鄉行悉隨處得以安身。度離抵達的陌會讓你覺得她是開熟擅於攀岩或正要迎接賴以維生的湖泊凍結的季節來臨,總是事物生dmi 和谐 源码想辦法安於變動之上的人。
她說自己無法待在不間斷的專訪著故走再循環反覆之中,無法輕易的吳俞溫馴安於所有已經能駕馭掌握的模式,比如一個城鎮的萱帶鄉行悉路線、閱讀一本書的度離抵達的陌眼光、甚至是開熟一首詩的完成。她在這些事物中放入自己的事物生瞬間就成為過去,若過於憐惜,專訪著故走再只會被圍困。吳俞溫馴
就算投入了五年多學習如何在民主學校擔任老師,萱帶鄉行悉在花蓮玉里學習阿美族的語言,見識到就算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玉里仍是島內的一個異鄉,是完全不理解的異質環境。她還意識到,自己需要啟程不停轉換互動的對象和環境,重新到達一個完全陌生、待解的場域,帶著敏銳的怎样打开app源码野性和必然會犯錯的決心,回到歸零的草創狀態。
問她在某個時間點會想要停下來嗎?完全不會。她立刻回答。
每次的停下,都是生命階段的無可預期,接管了接下來的流向。為了照顧罹癌的母親、孩子的出生,都讓她移轉了專注的重心,回應他們的需求成為支點。她要在身心已經不堪負重的垮落中,繼續奉獻心力給喜愛的事物,當作最重要的支撐,把被擠壓的痛苦丟進灰燼裡助燃,才讓心靈得以在困境中倖存下來。
她說在走出去,開始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相處、工作,才發現自己攜帶著早已內化的故鄉特質,比如工作結束,看見雇主還在勞動,就本能的覺得不能輕易地休息,就算規定的物业小区管理源码工作時間已經結束。仍然會收起自己的疲累,想要替對方多分擔一些。
這種覺得自己應該如此的進退、把「我」這個主詞取消的教養,本來一直都是她想要反抗的框架,但在面對實際的他人的時候,還是立刻覺察到這已經成為她行動時直覺的判斷,故鄉在此時已經不是一個地名或語言,而是形塑自己一部份意識的依據。
但她也說這種謹慎、善於花時間觀察收集資訊的慣性,讓她和先生在各國的民主學校工作時,不會立刻在還不理解全貌時就急於表態,而是嚴謹的把整合好的意見分享出去,在教育現場發揮最大的效益。
從獨自一人到和家人一起踏上旅程,她說跟孩子在路途中,自己總是非常有意識的知道每一分秒都是在創造和孩子之間珍貴的相處時刻,她希望孩子之後回想起來,可以感受到父母一直都陪伴著他一起成為這個世界的初學者,在各種文化面前都是懵懂的小孩,用這種視角來創造未來的鄉愁,這些經驗會長成他精神的盘面能量指标源码原鄉、家一樣的庇護所。
學習用當地的語言和不同來處的人對話,不僅僅是灌輸自己熟悉的世界、已知的知識系統給他,也不是一個已經安穩長好的地方,而是隨時都像地殼一樣在變動、鮮活的旅程,把孩子的意願也加入其中,和他一起問路、迷途、害怕,共享面對陌生的生嫩和笨拙。
當她帶著孩子做出選擇的時候,險境就來了。比如今天要不要搭上一輛陌生人的車?憑靠著蒐集來關於這個地區的安全程度,構成冒險的意志。
畢竟,險境也是命名而來的,她說。只要依心所至,如實經歷,就算最壞的狀況也是如此。為孩子也為自己,spring源码查看工具理解為何涉險,如何擔負每個動念的責任,慎重但無畏的對待每個際遇,如同她當時決定居家生產,她也深知這是包容了所有意外的選擇一樣,一切都僅是順路或逆行。
她對生存沒有恐懼。對她來說生存要素可以不斷簡化、去蕪存菁,隨時可以刪去多餘的選項,艱難的時候是和家人一起共同承擔選擇後的危險,不停製造出的不安定感讓伴侶有時難以承擔,不忍心看他因此受苦,讓她必須花一部分的力氣來保障足以支撐生活的收入,累積餘裕來安撫親愛之人難以落定的心。
回望這段旅程,甚至在過程中找尋什麼是非寫不可的事物的時候,她才發現自己並不全然了解故鄉,也在母親過世之後,才真正的在回憶中撿拾母親在身為母親之外的樣貌,直到母親再也無法跟自己緊密相連,無法再對她產生任何影響的時候,母親成為一個獨立而完整、充滿複雜人性脈絡的人,因為這個遙望的距離,她得以開始追問母親身上承襲的歷史是如何被塑造出來的,也因此開始走進這條重新認識故鄉的路徑。
而當她在教育現場親身參與學生的生命經歷之後,她更看懂了母親。看懂母親為何在自己年幼時,時常花三到四個鐘頭在電話中聆聽他人的話語,卻只是簡單應和,甚至保持沉默,像是無比審慎的珍惜每個說出來的詞語。
她走到這個人生階段才真正明白,我們其實都無法用太多意見涉入他人當下的處境,說出來的話也不需要懷有變造他人想法的企圖,明白在這樣的時刻安靜以待,是母親一路累積起來充滿厚度的智慧和慈悲。
她說孩子喜歡即興的規劃和行動這點,跟自己很像。現在她可以和孩子一起實踐和行動,拓寬更多的想像和自由,她希望用更貼近孩子思想的方式和他站在同一線,不管他做出的決定自己是贊同或反對,她都會選擇先跟孩子對話,對他的起心動念保持好奇,用問句逐步的帶領,讓他挖深想法興起的動機和之後對生活產生的全面更動,他是否都清楚的明白。
就像她父親曾經在她小時候,讓她站在一個被窗戶透進的光線照射的杯子面前,觀察影子呈現出不同深淺的漸層時一樣,父親把這個寬容的納入所有想法的空間交給了她,讓她可以在這個空間裡觀看如同隨著光影漸變的自我樣貌,現在她也轉交給了自己的孩子,想讓他保持彈性,用更多層次的視角理解這個多面的世界。
她曾經在書寫孩子降生到養育階段的散文集《逃生》寫道:「你看,水上有光在動,那是我本來的人生。」回到她自身來,我想知道她看見自己蒸發前,水上有光在動的經驗。
她說起飲下死藤水的經歷,那對她來說,是完全私密、獨有的體感,她讓自己不帶任何角色和身份的預判飲下它。那個位置甚至不是一個具體的環境,五天四夜只待在叢林裡的茅屋,把思想放掉,完全放空,虔誠的感受植物在身體裡的作用,聆聽它是否傳達出精微的訊息。
巫師告訴她,植物會回應她的渴望,是她能完全承擔的渴望。植物讓她去體驗純粹的空無,不強制掌控一定要擁有什麼樣的體驗,明白生命的流動和未知,不可能永遠都由自己主控。放自己失去重力,迎向從不能精確對時、生命的自然流動。她突然就覺得曾經的斷線都重新接通。我想她再也不用看著水面,感覺自己蒸發的不比它慢,水上仍然有光在動。
我最後請她形容一下現在的俞萱。她沒有養成回頭整理自己的習慣,但她發現歷年來出版的書名,能夠完全紀錄她在每個生命階段關注的母題。為了不讓自己過度的陷入曾經的細節和經驗,書名是一個能清楚代表那個階段的標記。
從最初的詩集《交換愛人的肋骨》,是強烈的希望從他人那裡交換深刻的東西。這種深情延續到《隨地腐朽》,都是她奉獻給所愛事物的親密交流。
之後的詩集《沒有名字的世界》和記錄在故鄉台東池上的散文集《居無》,則是她開始走出藝術,回到實際的生活和地景近身觀察,不完全依賴文字的描述,不輕易去定義。
學習面向工業化的城市,學習如何走進自然,拋棄她擅長的藝術化的語言,承認自己一直以來對這塊土地的一無所知。
而《逃生》這本散文集開頭的前兩篇,她回頭看才發現自己在書寫時全然沒有斷句,也完全反映了她當下成為母親之後被孩子填滿的時間,緊迫而陌生的狀況接踵而來,讓她根本無法換氣。逃生這個詞對當時的她而言,曾經是因為有了孩子而逃離了自己的生命,但漸漸從體內甦醒的對孩子的愛,讓她明白其實是孩子帶領著她逃向生命的新階段。
從回想自己交出肋骨的獻祭到帶著孩子到新墨西哥聖塔菲的忘形,她記錄下細膩的感受支撐自己的骨架,一切都僅此一次,不再回放。但她說一閉上眼睛,還是可以清晰的看見,有著母親和外婆,點亮著一盞熟悉餘溫的家。而她會繼續帶著它出走,再度離開一些熟悉的事物,抵達溫馴的陌生。
 Photo Credit: 九歌出版
Photo Credit: 九歌出版【加入關鍵評論網會員】每天精彩好文直送你的信箱,每週獨享編輯精選、時事精選、藝文週報等特製電子報。還可留言與作者、記者、編輯討論文章內容。立刻點擊免費加入會員!
責任編輯:馮冠維
核稿編輯:翁世航